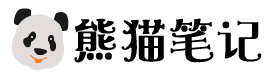注: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真实性有待确认,请自行甄别。
崇祯和他前面的皇帝比要强,那么怎么忘国,有论文吗?即使大厦将倾
发表于:2024-10-24 00:00:00浏览:8次
问题描述:即使大厦将倾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蒋德璟和皇上顶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中原一带的农民造反还没有平息,满州又闹翻了天。就在决定加税的一个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蹂躏二千里,掳掠人口牲畜五十余万,还在济南杀了一个德王。人家大摇大摆地杀了进来,又大摇大摆地满载而归,明朝的官军竟然缩做一团不敢跟人家交手。这样的兵岂能不练?练兵又怎能不花钱?不过皇上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皇上还听过另外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崇祯十一年考试选拔御史,一位来自基层的名叫曾就义的知县也说可以加税。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他们都廉洁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皇上觉得这种观点很对心思,便将他的考试名次定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据说曾知县为政廉洁,他的见解想必是有感而发,在逻辑上也绝对正确。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腐败等于一笔额外的重税。假设真能减去这笔“腐败税”,多派一些军饷当然无妨。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注2)。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们的佃户负担如何?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大政策了?这时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聚敛小人指的是谁?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他点出了一连串征税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感到这是搜刮百姓;同时他还点出了一连串兵马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明白练兵毫无成绩。搜刮了巨量的银子,却没有练出兵来,这究竟应该算聚敛还应该算练兵,已经不言自明了。
后边的话还长。总之是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财政部长主动站了出来,说本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皇上听了这话,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说话口音重,不擅长争辩,但是文章典雅,极其博学。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请注意这几句话。蒋德璟向皇帝描绘了一种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反叛。如此描述这个转弯,带了点现代边际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确实没有如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他们显然意识面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拐弯。这个死弯在我们两千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命了。 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在我看来,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二、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社会集团来说,崇祯死弯的谷底是在不同的时刻出现的。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地方。至于确切时间,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为标志,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关于发生在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过三种说法。其中与政府催粮派款联系最为直接的说法,出自毛奇龄的《后鉴录》卷五。毛奇龄是《明史·流寇传》的撰写人,算得权威人物了。他说“自成......相推为里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李自成被村民推选为行政村的村长。明末征收税费的途径和现在差不多,也是通过村干部进行的。钱粮交不齐,拿村干部是问。毛奇龄说:“值催科急,县官笞臂,枷于市。”明朝有一套固定的催粮派款的办法,这里记载的“笞”——打板子,“枷”——戴上木枷在大街上示众,都是“催科”的常规程序。按照这种程序,逾期未完税的,每隔五天十天便要打一顿或者枷上示众一回,直到你完成政府分派的交纳任务为止。如果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自己又赔不起,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李自成正是如此。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为寇。” 按照这种说法,李自成也是被政府的赋税逼反的,不过中间经了当地一个叫艾同知的乡绅之手。所谓乡绅,大体是指那些退休或养病在家,有干部身份或者叫干部任职资格的地主。所谓“应甲之债”,是在支应政府派到村里的差役时欠下的债务。大概李自成为了支应官府,找艾同知借了债,恰好赶上灾年,一时还不起,被有权势的财主往死路上逼,于是反了。 从名义上说,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所有的乱收费乱摊派都并入了一个总数,不应该再有什么额外的支应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总有办法征收额外的钱粮,更何况中央政府也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在偏僻一些的地方,地方政府竟敢公然签派各种额外的追索,连借口都懒得找。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为政府驿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俗名黄来僧。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岁便到驿站当了驿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中央政府背不起驿站这个邮局兼招待所的巨额亏损,便下决心大规模裁减驿站。次年,二十四岁的李自成下岗失业。 我罗罗嗦嗦地罗列了三种版本,是因为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死弯的形状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失业下岗的影响等等。 天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明末的大乱从陕西开始,这一点很有自然地理方面的道理。据说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想必降雨区域普遍南移。从气象记载来看,就表现为陕西一带连续多年的大旱,动辄七八个月不下雨。在陕西那个靠天吃饭的地方,这意味着大面积的饥荒。明朝曾有人观察到一个现象:江南的米价从每石四五钱银子涨到每石一两五到二两银子的时候,路上就可以看到饿殍了。而在李自成造反前后,陕北的米价在每石六两到八两银子的超高价位徘徊不落,与此相应的就是饿殍遍地和大量的人相食的记载。更何况陕西不比江南,底子本来就很薄,哪里架得住这样连年的天灾。 到了这种关头,官府应该做的是救济和赈灾,绝不应该继续加税压榨。而崇祯所做的正是加税,而且催逼严厉。《明史·流贼列传》记载说:当时陕西所征的名目有新饷、间架、均输,名目恨不得每天都有增加,而且腐败的吏胥们因缘为奸,民大困。李自成在造反的第一个版本中挨县官的板子,戴枷示众,就很好地体现了官府火上浇油的作用。 按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规定,各地遭灾,地方官一定要及时报告,隐瞒不报者死。如果情况紧急,地方官有权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中央政府自然更有赈灾的责任。这是合乎儒家治国理论的正式规定,但不过是一纸规定而已。据《明史·流贼列传》记载,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国防部里的局长)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一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求国库发放十万两银子赈济饥民。结果“帝不听”。皇上不听,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对明朝的皇帝来说,朱元璋是他们的祖宗,祖训的地位相当于如今的宪法,但皇上就是违宪了,谁又敢拿他怎么样? 话又说回来,各地的粮仓里也未必有多少粮,好多地方账面上有,实际已被那些冗官冗兵偷偷吃了黑了,或者换成糟朽了。李自成围困开封的时候,开封的粮仓就露出了这样的黑馅,结果开封大饥,一个人单身走路经常失踪,被人像偷鸡摸狗一样悄悄杀了吃掉。我国粮食部门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难道崇祯就能找到根治的灵丹妙药?
李继贞申请赈灾的十万两银子并不是大数,大体相当于皇室三四个月的伙食费。再说,那几年仅仅加征辽饷这一项,陕西百姓就多掏了26万两银子。比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饷来,比起即将发生的许多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战役和高级将领的胜利或者自杀来,这些钱粮方面的小数字不过是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这些零碎中,在人们无可奈何的官府腐败和官家冷漠中,崇祯死弯已经已经逼近了的谷底。我看到过一句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注5)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却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一般说来,赋税加重意味着皇上豢养的专政工具更加强大,老百姓造反的风险也应该随之加大。尽管从钱粮变成威慑的转化渠道腐败朽坏,严重渗漏,那一大笔钱粮总要变出一些军队和刀枪,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面前,并且在心怀不满的百姓面前晃动,构成冷飕飕的威胁。可是,如果压榨过度,老百姓到了横竖也是一死的地步,风险就无法继续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灵了。万一官府的镇压力量跟不上劲,或者外强中干,或者可以收买,让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乱倒是一条活路,这时候,崇祯死弯就见了底。在这块地方,造反有收益,当良民却没有。造反有风险,但良民同样有,说不定还更大。这就是崇祯死弯形成的微观基础。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政府与民间冲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垄断了所有权力,压榨老百姓,这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百姓一盘散沙,根本抵挡不住,这个社会迟早要沉落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内容就是如何对付政府,不同的对策有什么样的风险和前景。继续赶路无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与造反比起来,吴广认为二者的风险差不多,仍是一个死。陈胜说天下苦于秦朝的统治已经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于是决定造反。通过这个我们已经熟悉的计算,可以断定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死弯的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后来陈胜吴广对同伙做了一个的动员报告,大讲众人的“谷底”处境。这大概是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最早的造反动员报告。 员报告说: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赶到了。误期就要砍头。就算不砍头,戍边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干大事出大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人赞成这个结论,于是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 这是公元前209年发生的事情,但这类事情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重复着。政府和百姓的这种致命的冲突,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体制性的解决。我们的祖先竟好像记吃不记打一样,总在同一个问题上犯错误。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已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计算凶吉。他想入伙造反,又怕风险大。留在寺院里,又迟早要给官军捆去请赏。正在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的哥们儿汤和托人带给他一封信。信中说,他投奔了红巾军,已经当到千户(类似现在的团长)了,劝朱元璋也去入伙。朱元璋烧掉信,犹豫了好几天,同屋的师兄悄悄告诉他,前天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发。(注7)
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走投无路,接近崇祯死弯的谷底了。但是朱元璋办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里和另外一个哥们儿商量。他的问题是:是在庙里等着人家抓呢,还是起来跟他们拼了?(注8)那位哥们儿认为还是投红巾军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劝他回去向菩萨讨一卦,听菩萨的。朱元璋回到寺院,发现寺院被烧光了,和尚们也跑光了。据说官军认为红巾军供奉弥勒佛,和尚也供奉弥勒佛,怕和尚给红巾军当间谍,就挨着班烧寺院。这天正好烧了朱元璋的安身之处,他没了吃饭的地方。谷底到了。朱元璋还是讨了一卦。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当时的口语与现在非常接近,这敢不敢的问答是史书记录的原话,并不是我的翻译。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入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政府大院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注9)。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在我看来,张知县死得颇为冤枉。他怎么会死呢?按照官方理论的说法,这类恶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朱元璋来自贫苦大众,本人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中的一块有名的石头,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亲情是怎么回事,也很注意强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有赈灾方面的漂亮规定,那就是亲情的证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规定,坐在大堂上的张知县应该正在放粮而不是催粮。下边应该有颂声一片,怎么竟冒出一群黑脸的持刀大汉呢?谁都明白,开仓放粮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况放粮又不是放他张家的粮。难道张斗耀这家伙有毛病,不喜欢用别人的钱给自己买好,偏偏要冒险得罪人,替别人讨债么?或者他别有苦衷?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任务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这是用胡萝卜勾引毛驴前进的政策。同时还有大棒驱赶的政策。完不成钱粮任务要降级,还要扣罚俸禄。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扣罚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而且参与考成的完粮纳税指标不仅是正额辽饷,后来又加上了许多杂七杂八的项目。其内容之庞杂,连户部(财政部)的局长们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体登记办事的书手处理如此说来,县官催比钱粮,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资和乌纱帽毕竟在人家手里,而不在老百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知县们如何是好呢?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也是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是在崇祯即位前一年被杀的,我们不好把导致张知县死亡的责任扣到崇祯头上,但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也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比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注11)。中央政府设置的赏罚格局如此,张知县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简单问题: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资重要,还是某个欠税农民的屁股重要?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既然财政部的司局长们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便很有可能蒙混过关。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钱粮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帐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长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上前边。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资,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这显然是一个调动广大衙役追讨欠款积极性的好办法。崇祯十三年除夕前,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声载道。没想到衙役们的积极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入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蠹”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们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蠹”运动扩充为“除五蠹”运动。其中既包括了州县的吏胥衙役
栏目分类全部>